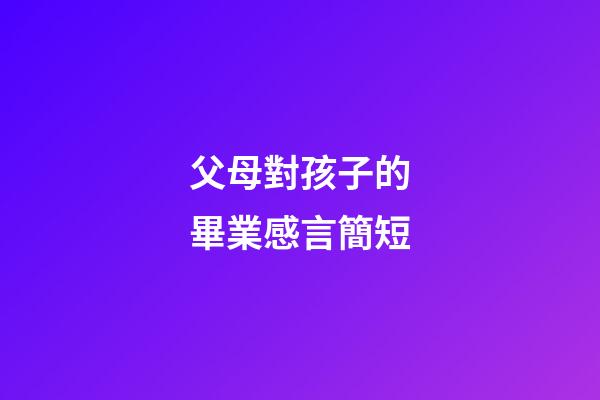管建剛推敲聽課感言
語文課應該是“閱讀本位”,還是“寫作本位”
——兼與管建剛老師商榷 “閱讀本位”的語文課,以培養閱讀能力為取向,重文本內容的理解、感悟和積累。
以葉圣陶先生為代表的主流讀寫觀認為:“閱讀是寫作的基礎”“寫作的‘根’是閱讀”“培養讀的能力,也是一個目的”“教師教得好,學生讀得好,才能寫得好”。
“寫作本位”的語文課,以培養寫作能力為取向,重文本形式的理解、感悟和運用。
潘新和先生在《語文:表現與存在》一書中顛覆性地提出了“寫作本位說”,他提出,“閱讀,指向言語表現,指向寫作”“寫作是閱讀的目的”“寫作是閱讀能力的最高呈現”。
管建剛老師的語文課無疑是“寫作本位”的,他在閱讀教學上的探索勇氣可嘉,也有一定的價值。
管老師的語文課與《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注重“語言運用”的精神一脈相承,改變了傳統語文課“重閱讀輕表達”的傾向,做到了“與內容分析式的語文課說再見”。
曹文軒教授在參加了“全國第九屆青年教師閱讀教學觀摩活動”后指出:“兩天半的觀摩課聽下來,講課老師對文本的分析往往停留在字詞上或是對題旨的理解分析和解釋上,較少回到文本的形式上。
回到文本的寫作藝術上。
有些課會涉及一點點,我以為是遠遠不夠的。
講課文,不能不講文章之道,不能不講文章之法。
” 管建剛老師的語文課強化“表達意識”,大講“文章之法”,這個取向是正確的。
但“真理多走一步,就會變成謬誤”。
管建剛老師的語文課把“寫作”推向了極致,課堂充滿了理性,毫無情趣。
這樣的語文課,學生會喜歡嗎
于永正老師說得好:“少一些理性,多一些情趣,讓學生愛上語文課”。
姑且承認學生喜歡管建剛老師的語文課,滿心接受管老師傳授的“文章之法”。
但仔細推敲管建剛老師在《理想的風箏》一課中傳授的“文章之法”,大有問題。
管建剛老師可能沒有讀過蘇叔陽先生《理想的風箏》的原文。
蘇教版的“編者”對蘇叔陽先生的原文作了不少刪改,其中在劉老師“寫板書”后刪掉了這樣兩段文字:他的課講得極好。
祖國的歷史,使他自豪。
講到歷代的民族英雄,他慷慨陳詞,常常使我們激動得落淚。
而講到祖國近代史上受屈辱的歲月,他自己又常常哽咽,使我們沉重地低下頭去。
后來,我考入了歷史學系,和劉老師的影響有極大的關系。
他不喜歡筆試,卻喜歡在課堂上當眾提問同學,讓學生們述說自己學習的心得。
我記得清楚極了:倘若同學回答得正確、深刻,他便靜靜地佇立在教案一側,微仰著頭,瞇起眼睛,細細地聽,仿佛在品味一首美妙的樂曲,然后,又好像從沉醉中醒來,長舒一口氣,滿意地在記分冊上寫下分數,親切、大聲地說:“好
五分
”倘若有的同學回答得不好,他就吃驚地瞪大眼睛,關切地瞧著同學,一邊細聲說:“別緊張,想想,想想,再好好想想。
”一邊不住地點頭,好像那每一次點頭都給學生注入一次啟發。
這時候,他比被考試的學生還要緊張。
這情景,已經過去了將近三十年,然而,今天一想起來,依舊那么清晰,那么親切。
我們要向學生傳授的是蘇叔陽先生的“文章之法”,還是“編者”的“文章之法”
答案不言自明。
因為“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取法乎下,其下下矣”。
而管建剛老師向學生傳授的是“編者”的“文章之法”。
請看管老師“構思一:故事,兩個兩個”的教學片段:師:課文寫了四個故事——(生讀板書:講故事、寫板書、放風箏、追風箏。
)師:課文用四個故事來寫人,記住:用故事來寫人。
(板書:用故事來寫人。
生讀)師:放風箏、追風箏,這兩個故事,都是發生在課余的。
講故事、寫板書,都是發生在——生:課上的。
師:作者寫了四個故事,兩個故事發生在課上,兩個故事發生在課余,你說這是巧合,還是作者有意的安排
生:有意的。
師:有意的安排,這就叫“構思”。
其實,蘇叔陽先生寫劉老師的故事不是課上兩個,課余兩個,而是課上三個。
只不過劉老師“課上關愛學生”的故事被“編者”刪掉了。
嚴格地說,課余的兩個故事——放風箏、追風箏,應該是一個故事——放風箏。
蘇叔陽先生的過渡段明明白白地寫著:“然而,留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劉老師每年春天的放風箏”。
管建剛老師為了與課上的兩個故事相“對稱”,刻意將它分成兩個故事。
寫文章是要講究“對稱美”,但不宜將“對稱美”作為教條教給學生。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管建剛老師“構思二:故事,一長一短”的教學:師:你看,“課上”的兩個故事:一長一短,先長后短;“課余”的兩個故事:一長一短,先長后短。
這是巧合,還是有意
生:有意的。
師:可能有的同學,覺得也可能是一種巧合。
那么,我們再看第四自然段。
第四自然段,有一句話,寫劉老師的外貌,找到了嗎
指給我看。
師:(快速巡視)對,請一起讀。
師:嚴格來講,這不是寫“講故事”的,同意不
生:同意。
師:第四自然段,剛才統計過了,
【第13句】:5行,減去第一句話的
【第2句】:5行,寫講故事的,其實是11行。
【生讀板書:講故事(11行),寫板書(7行),放風箏(11行),追風箏(7行)。
】師:我一個字、一個標點地統計了:“講故事”11行218字“寫板書”7行 137字“放風箏”11行 217字“追風箏”7行 135字兩個故事,一長一短,行數相同,字數也幾乎一樣。
這不是教條,這簡直是“刻板”。
請管建剛老師認真讀讀蘇叔陽先生的原文,真的是這樣嗎
寫文章是要講究對段落長短的安排和控制,但寫文章真的要“刻板”到如此地步嗎
管建剛老師“構思三:故事,內在的關聯”的教學細細推敲,也問題多多:師:課文的題目是“理想的風箏”,顯然,“放風箏”“追風箏”,一定要寫。
——劉老師“上課”的故事,肯定有很多,作者選了“講故事”“寫板書”這兩個。
請問,能不能換成劉老師“關心同學”,比如,有同學受涼了,劉老師脫下自己的衣服,給同學披上;換成劉老師“博學多才”,會彈琴、會畫畫呢
(生沉思)師:請你默讀第八、第九自然段,“放風箏”“追風箏”里的劉老師,是個怎樣的人
生:是個樂觀、頑強的人。
師:如果上課的故事,換成劉老師“關心同學”“博學多才”,與“放風箏”“追風箏”,搭不搭配
生:不搭配了。
師:猜一猜:上課的故事,應該寫出劉老師的什么特點,才跟后面的“放風箏”“追風箏”,特別“搭”
生:也應該是寫出劉老師的樂觀、頑強。
師:現在,請你默讀“講故事”“寫板書”,這兩個故事,是不是也寫出了劉老師的樂觀、頑強。
生:這兩個故事寫出了劉老師的樂觀、頑強。
師:(指板書,生讀)講故事,寫板書,放風箏,追風箏。
師:這四個故事為什么能放在一起
——它們有內在的聯系,都指向了劉老師的樂觀、頑強。
用故事來寫人,要注意故事,有沒有這樣的內在的聯系
(生點頭)管建剛老師錯把“編者”刪改的文章當作蘇叔陽先生的原文。
蘇叔陽先生寫此文就是只表現劉老師的“樂觀頑強”
人性是多元的,豐富的,不要把人物的性格一元化。
人物性格一元化的文章不是好文章,經典文本都會寫出人性的豐富和復雜。
蘇叔陽先生恰恰在原文中寫了管建剛老師認為與放風箏、追風箏“不搭”的內容——劉老師的“博學多才”“關心同學”。
因為劉老師對蘇叔陽先生最大的影響是“他的課講得極好……”以致,“后來,我考入了歷史學系,和劉老師的影響有極大的關系。
”蘇叔陽先生記得最清晰的情景是劉老師課上對學生的關愛。
這一段寫得極好,劉老師的語言、動作、神情,惟妙惟肖,畫面感很強。
蘇教版“編者”刪掉這一段,真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綜上所述,管建剛老師的《理想的風箏》的教學向學生傳授的是低水準的“文章之法”,不是蘇叔陽先生真正的“文章之法”。
難怪有老師尖銳地指出,管建剛老師還不如拿小學生優秀作文或老師的下水文來教學,這樣更為直接有效。
恕我直言,如此教學培養出的學生也許能寫出報刊雜志上發表的“優秀作文”,但長此以往,貽害無窮,因為這是對學生寫作靈性的桎梏。
我十分贊成語文課要講“文章之法”,但我還想說,不是所有的“文章之法”都可以言說。
應該承認,不少“文章之法”往往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那怎么辦
先讓學生將好文章熟讀,背下來,儲存在腦海中。
就像管建剛老師說的,先讓學生“懷上”,至于“用”,得允許學生有一段“孕”的時間。
巴金先生10歲時就可以將《古文觀止》里的200多篇文章背下來。
他在晚年時說,他之所以后來成為作家,寫出那么多的小說、散文,全靠當年背誦的那200多篇文章墊底。
我以為,“閱讀本位”、“寫作本位”最好不要走極端,“兩極相融”最為理想。
王崧舟老師的閱讀教學探索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
2010年,王老師執教《與象共舞》,分別闡釋了“閱讀本位”和“寫作本位”的語文課。
2011年王老師執教《望月》,2012年王老師執教《去年的樹》,實現了“兩極相融”。
去年下半年,我在無錫現場聆聽了王崧舟老師執教的《去年的樹》。
閱讀與寫作水乳交融,“文章之法”的傳授清晰可見,又毫無生硬、機械之感。
王崧舟老師在課后報告中談到了三個融合,那就是:學習語用和陶冶情感相融合;學習語用和理解內容相融合;學習語用和滲透學法相融合。
這三個融合就是閱讀本位與寫作本位的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讓我們謹記王崧舟老師的警語:“放棄了情與境的語文學習是機械的語言文字訓練。
” 最近,我在讀《蔣勛講〈紅樓夢〉》。
蔣勛先生常常指出曹雪芹創作的奧秘,但也闡發閱讀感受,即所謂的興發感動。
我以為,語文課亦當如此。
附:蘇叔陽《理想的風箏》原文春天又到了。
柳枝染上了嫩綠,在春風里盡情飄擺,舒展著自己的腰身。
連翹花舉起金黃的小喇叭,向著長天吹奏著生命之歌。
而藍天上,一架架風箏在同白云戲耍,引動無數的人仰望天穹,讓自己的心也飛上云端。
逢到這時候,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劉老師,想起他放入天空的風箏。
劉老師教我們歷史課。
他個子不高,微微發胖的臉上有一雙時常瞇起來的慈祥的眼睛,一頭花白短發更襯出他的忠厚。
他有一條強壯的右腿。
而左腿,卻從膝以下全部截去,靠一根被用得油亮的圓木拐杖支撐。
這條腿何時、為什么截去,我們不知道。
只是有一次,他在講課的時候講到女媧氏補天造人的傳說,笑著對我們說: “……女媧氏用手捏泥人捏得累了,便用樹枝沾起泥巴向地上甩。
甩到地上的泥巴也變成人,只是有的人,由于女媧甩的力量太大了,被摔到地上摔丟了腿和胳膊。
我就是那時候被她甩掉了一條腿的。
”教室里自然騰起一片笑聲,但笑過之后,每個學生的心頭都飄起一股酸澀的感情,同時更增加了對劉老師的尊敬。
他只靠著健壯的右腿和一支圓木棍,一天站上好幾個小時,為我們講課。
逢到要寫板書的時候,他用圓木棍撐地,右腿離地,身體急速地一轉,便轉向黑板。
寫完了粗壯的粉筆字,又以拐杖為圓心,再轉向講臺。
一個年過半百的老師,一天不知要這樣跳躍旋轉多少次。
而他每次的一轉,都引起學生們一次激動的心跳。
他的課講得極好。
祖國的歷史,使他自豪。
講到歷代的民族英雄,他慷慨陳詞,常常使我們激動得落淚。
而講到祖國近代史上受屈辱的歲月,他自己又常常哽咽,使我們沉重地低下頭去。
后來,我考入了歷史學系,和劉老師的影響有極大的關系。
他不喜歡筆試,卻喜歡在課堂上當眾提問同學,讓學生們述說自己學習的心得。
我記得清楚極了:倘若同學回答得正確、深刻,他便靜靜地佇立在教案一側,微仰著頭,瞇起眼睛,細細地聽,仿佛在品味一首美妙的樂曲,然后,又好像從沉醉中醒來,長舒一口氣,滿意地在記分冊上寫下分數,親切、大聲地說:“好
五分
”倘若有的同學回答得不好,他就吃驚地瞪大眼睛,關切地瞧著同學,一邊細聲說:“別緊張,想想,想想,再好好想想。
”一邊不住地點頭,好像那每一次點頭都給學生注入一次啟發。
這時候,他比被考試的學生還要緊張。
這情景,已經過去了將近三十年,然而,今天一想起來,依舊那么清晰,那么親切。
然而,留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劉老師每年春天的放風箏。
北方的冬季漫長而枯燥。
當春風吹綠了大地的時候,人們的身心一齊蘇醒,一種舒展的快意便浮上心頭。
當沒有大風、而且晴朗的日子,劉老師課余便在校園的操場上,放起他親手制作的風箏。
他的風箏各式各樣:有最簡單的“屁簾兒”,也有長可丈余的蜈蚣,而最妙的便是三五只黑色的燕子組成的一架風箏。
他的腿自然不便于奔跑,然而,他卻絕不肯失去親手把風箏送入藍天的歡樂。
他總是自己手持線拐,讓他的孩子或學生遠遠地擎著風箏。
他喊聲:“起
”便不斷抻動手中的線繩,那紙糊的燕子便抖起翅膀,翩翩起舞,直躥入云霄。
他仰望白云,看那青黑的小燕在風中翱翔盤旋,仿佛他的心也一齊躍上了藍天。
那時候,我常常站在他旁邊,看著他的臉,那浮在他臉上甜蜜的笑,使我覺得他不是一位老人,而是一個同我一樣的少年。
當一天的功課做完,暮色也沒有襲上校園的上空,常常有成群的學生到操場上來參觀他放風箏。
這時候,他最幸福,笑聲朗朗,指著天上的風箏同我們說笑。
甚而至于,有一次,他故意地撒脫手,讓天上飛舞的紙燕帶動長長的線繩和線拐在地上一蹦一跳地向前飛跑。
他笑著、叫著,拄著拐杖,蹦跳著去追趕繩端,臉上飄起得意和滿足的稚氣。
那天,他一定過得最幸福、最充實,因為他感到他生命的強壯和力量。
這情景使我深深感動。
一個年過五十身有殘疾的老師,對生活有著那樣純樸、強烈的愛與追求,一個活潑潑的少年又該怎樣呢
不見到他已經近三十年了,倘使他還健在,一定退休了。
也許,這時候又會糊風箏,教給自己的子孫,把那精致的手工藝品送上天去。
我曾見過一位失去了一條腿的長者,年復一年被斷腿釘到床上,失去了活動的自由。
我希望他不至于如此,可以依舊地仰仗那功德無量的圓木棍,在地上奔走,跳躍,旋轉,永遠表現他生命的頑強和對生活的愛與追求。
然而,倘使不幸他已經永遠地離開我……不,他不會的。
他將永遠在我的記憶里行走、微笑,用那雙寫了無數個粉筆字的手,放起一架又一架理想的風箏。
那些給了我數不清的幻夢的風箏將陪伴著我的心,永遠在祖國的藍天上滑翔。
劉老師啊,你在哪里
我深深地、深深地思念你……